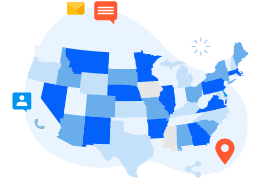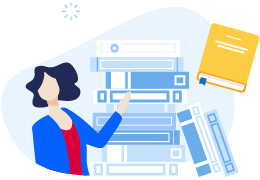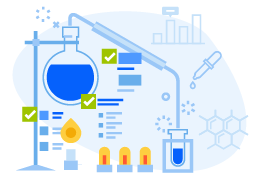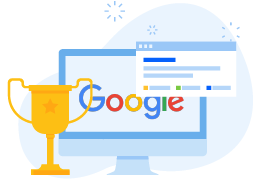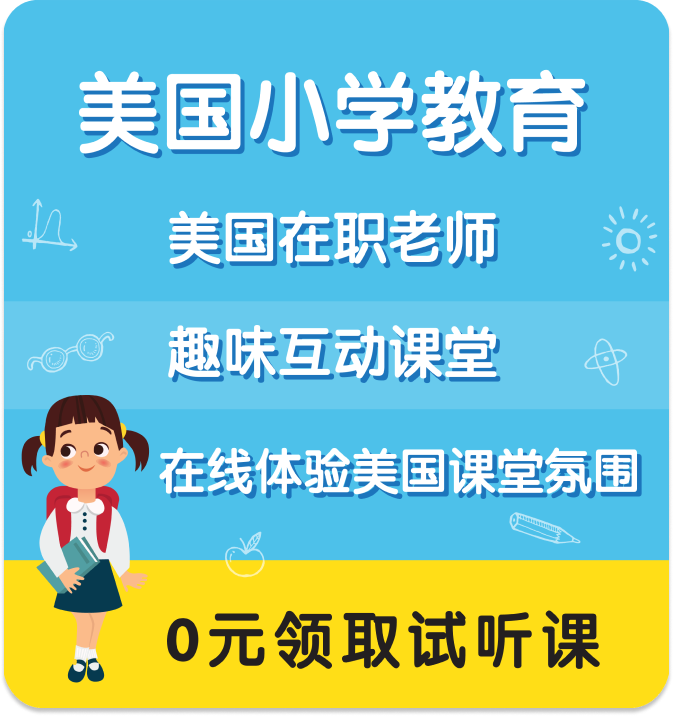访学归来曹天宇刻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清华印象
“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自2010年起设立,受到“985”基金和校基金会的共同支持,为博士生赴国外一流大学或重要国际组织、师从一流导师开展研究工作提供4-6个月的生活费资助。至今已有超过1200名博士生获得基金支持。该基金受到师生欢迎,博士生普遍反映受益匪浅。
每个参加短期访学的博士生都有一段不可复制的、特别的经历,我们将不定期与大家分享他们精彩的访学故事。
亲,哪天能看到你的故事呢?
有幸受“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资助,我前往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Chemical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Raymond J. Gorte课题组进行短期学术访问。
Gorte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能源转化与催化科学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首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生物质脱氧提质、催化裂解制氢等多个方面。他是第一个将丙烷(C3H8)和丁烷(C4H10)等复杂碳氢化合物引入燃料电池系统的研究者,为燃料电池系统续航能力的增加和应用范围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消解复杂碳氢化合物转化带来的积碳问题,Gorte教授还发展了浸渍纳米电极催化体系,也是目前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研究的重要方向。而我的博士课题正是使用固体碳燃料驱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此次访学将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有所助益。
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兰克林塑像前
直接碳燃料电池是一种依托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实现由固体碳燃料向电能直接转化的技术路线,具有发电效率高、排放水平低的优势。面对我国“贫油、富煤、少气”的能源现状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用廉价易得的固体碳燃料实现高效清洁发电,无疑是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能的可行技术路线,在国际上也吸引了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但是,直接碳燃料电池的技术成熟度还比较低,碳燃料与固体电极之间有限接触问题,是限制直接碳燃料电池性能提高的主要因素。为了增强电极与碳燃料的接触,Gorte教授创造性地使用液态金属锑作为电极,将原有的电极与燃料之间的接触从固-固接触改善为液-固接触。良好的接触条件使得电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带电离子传导得以进行,帮助直接碳燃料电池获得了较好的发电性能。但是在长周期运行过程中,教授发现生成的锑金属氧化物(Sb2O3)容易与电解质(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陶瓷)之间发生反应,两者形成共熔体,破坏电解质隔膜的整体性。其主要后果是电解质腐蚀减薄,最终造成燃料电池密封失效、系统寿命耗尽。但是在长期的研究中,电解质的腐蚀机理并不清楚、形成共熔体的证据也不充分,这使得对于此类型电解质高温电化学腐蚀的防治无从入手,成为限制直接碳燃料电池技术推进的瓶颈问题。
我个人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以液态金属锑作为阳极的直接碳燃料电池。在前期的研究中,我已经对锑金属及其氧化物在电极中的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借助于这一基础,我迅速理解了教授的研究意图,并在实验室已有元器件的基础上搭建了我自己的实验设备。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我与实验室的同学深入讨论实验操作的技巧,迅速熟悉了实验设备的操作方法,并克服了实验器材短缺、设备操作不熟练、表征技术不足等等困难,创造性地改装了实验室现存的工具元件,以满足长时间实验的要求。同时,依托于三年来对反应体系的了解和操作经验,我预见和规避了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节约了实验原料和时间。
在努力推进实验的同时,我没有放松对文献的检索,深入阅读并剖析了课题组此前的文章。我认为,在Gorte教授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工作中,燃料电池的性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实验架构是简便易行的,数据报道是详实可信的;不能明确高温电化学腐蚀机理的主要原因,是表征手段选择不当、数据处理不细致——课题组仅仅采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了电极和电解质之间的界面,这既不能明确电化学反应界面附近的元素组分分布,也不能观察到运行之后电解质陶瓷晶形的变化。即使在没有正式发表的实验记录中有发现电解质结构产生变化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照片,其放大倍率依然不足以辨别电化学腐蚀发生的位置和腐蚀的方式。针对这一情况,我联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材料系表征中心,计划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陶瓷电解质在工作前后的微观结构变化,同时使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EDS)表征界面附近的、特别是微观条件下的元素分布。
我通过实验获取了直接碳燃料电池的连续运行数据,复现了前期文献中观测到的实验现象,并通过切割和抛光,把冷却后的电化学反应界面制成供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使用的样品。在高倍率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帮助下,我观察到了陶瓷电解质在运行前后的变化:在运行前,陶瓷晶体连接紧密,电解质完整度高;但是经历长时间的电化学反应之后,陶瓷晶粒之间的连接减弱,电解质的整体性变差。为了了解电解质晶粒连接减弱的原因,我通过X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表征了电解质陶瓷晶界部位的元素分布,并发现锑元素进入到了陶瓷电解质之中,并在陶瓷的晶界处富集,晶界处过高的锑元素分布在钇元素和锆元素的背景中非常明显。这使得我深信,燃料电池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氧化锑攻击了氧化锆电解质陶瓷的晶界,沿着晶界向电解质陶瓷晶体内部迁移,削弱了陶瓷晶粒之间的联系,最终破坏了陶瓷的整体性。在Gorte教授的严谨指导下,我又重复了实验,观察到了相近的现象。
为了弥补研究上的空白,我在完成了依托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陶瓷(YSZ)电解质的实验与表征之后,转向了另一类运用广泛的电解质材料:氧化钆掺杂的氧化铈(GDC)。在前期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将氧化钆掺杂的氧化铈运用于液态锑金属直接碳燃料电池的运行。但是对于这类电解质的长时间实验和稳定性报道一直处于空白。为此,我专门制备了以氧化钆掺杂的氧化铈为电解质的直接碳燃料电池,并依托控制变量法对该型燃料电池进行了测试。表征的结果表明,电化学反应生成的氧化锑,同样会通过晶界进入氧化钆掺杂的氧化铈电解质内部,对燃料电池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对于两种陶瓷电解质的实验测试和表征表明:锑元素沿着晶界向电解质陶瓷内部迁移的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解决这一问题,对延长电解质寿命、提高直接碳燃料电池运行的可靠性有重要而广泛的意义。
为了彻底明确氧化锑迁移与电解质陶瓷之晶界间的关系,我在Gorte教授的指导下,试图排除晶界的影响,对直接碳燃料电池展开测试。在此次试验的设计过程中,我采用了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单晶作为燃料电池的电解质。由于单晶只有一个晶粒,因此在电极-电解质界面没有晶界的存在,锑元素在燃料电池运行过程中沿着晶界向电解质内部的迁移将得以杜绝。实验的进展正如同我们预料的那样:采用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陶瓷单晶作为电解质的直接碳燃料电池在运行过程中表现稳定。即使通过了较大的电流和较多的电荷,燃料电池的电化学性能依然保持不变。实验完成之后的高清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也表明,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单晶电解质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微观结构的变化,电解质的厚度和形貌没有显示出高温电化学腐蚀的迹象;X射线光电子能谱也没有在氧化钇稳定的氧化锆单晶电解质找到锑元素。这一测试结果显示,锑元素向电解质内部迁移是电解质陶瓷失去完整性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迁移是通过电解质陶瓷内部的晶界进行的。
对我得出的以上结论,Gorte教授非常的重视,这一发现回答了一个五年以来悬而未解的问题:电解质陶瓷是如何被液态金属电极在高温下腐蚀的。为此,Gorte教授同时请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I-WeiChen和高温反应进展专家、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教授John Vohs。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继续补充了实验和表征的结果,完善了高温下锑元素通过电解质陶瓷晶界向电解质内部迁移的理论。经过Gorte教授与我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能动系的史翊翔副教授的商议,我们决定把形成的文章投稿给国际陶瓷期刊(CeramicsInternational)作为重要的陶瓷领域科学进展发表。国际陶瓷期刊是国际上排名第二的同行评议陶瓷科学期刊,排在欧洲陶瓷学会会刊(Journal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之后和美国陶瓷学会会刊之前(Journal of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目前该文章已得到了审稿意见回复,从意见本身来看,国际同行对此次研究的问题以及结论是非常认可的。
实验室的实验台架前
通过这次海外短期学术访问,我提高了自身的科研水平、对具体的科学问题给出了答案,为推进直接碳燃料电池这项技术的前进作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给Gorte教授留下了非常好的“清华印象”。
清华每年向北美高校输送了大批的研究生,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在进入美国顶尖名校之后迅速地迷失了自我,人生的理想和志向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以Gorte教授课题组为例,他共接收过三名清华毕业后来到宾大深造的学生,除去一人因个人志趣变化与教授不欢而散之外,另一人在实验中出现重大偏差,造成期刊文章的撤稿,还有一位因捏造数据被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打入另册。这些学生的表现令教授对清华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惑,也给我当时的申请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在知悉这一情况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痛心疾首:能够申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清华毕业生,在本科时期几乎是师长眼中的“骄子”、朋辈眼中的“精英”、后辈眼中的“大神”,然而这些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选择却让我大跌眼镜。因此,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工作和学习上都非常谨慎,希望扭转教授对于清华这种不真实的印象。在一组组实验、一次次讨论、一封封邮件之中,我能感受到教授对于清华的印象在逐渐改善;而在科研取得一定进展之后,Gorte教授发现清华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术水平上不输自己课题组内的学生,在辩证思考、设计实验和仔细观察等方面甚至还有超越。在我结束此次短期访学的时候,教授终于对清华开始采取一种信任和欣赏的态度。
此次短期访学,我的收获不仅局限于学术上,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也进行了一定的考察。我认为,相较于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方式,宾大的优点在于博士生间的学术交流非常密切。这样的交流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较正式的学术报告,每周五的中午在系里的报告厅举行。会上,在读博士生会根据自己的博士课题向教授和博士生同学们做报告,这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必须环节。其实,这样的报告在清华也并不少见,但是宾大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博士生听报告的鼓励态度:主办报告的院系办公室会为参加学术报告的同学和老师准备午餐,利用午餐时间开展学术交流,还能获得一顿“免费的午餐”,这样的安排对学生还是有吸引力的。另一种由学生会主办的交流方式则随意得多,交流的同时,在院系的活动室准备上水果、零食、冷饮和啤酒,供同学们自由取用。利用每周四的这样一段“开心时间”,大家可以自由组队,交流最近的科研心得、排解忧愁烦闷,还能互相交换实习和就业信息,很受博士生们欢迎。我个人从读博士以来就非常注重学术上的交流,并且,这种学术交流应当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博士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聆听“大牛”宽泛的说教,或瞻仰“成功人士”的神迹。宾大的两种交流形式很好地满足了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沟通需求。
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博士培养中,沟通问题是最大的短板。语言障碍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沟通意识。中国的学生往往比较羞涩,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埋头苦干。这通常是因为中国学生心里存在着两种担忧:一者,求助他人,会欠下人情;再者,我提出这种简单的问题,会让人瞧不起。这两种心结阻碍了中国学生与课题组内教授、同学之间的沟通,陷入无休止的单打独斗,让教授、同学既觉得这个人很神秘,又觉得这个家伙效率低、产出少。其实,向人请教总会欠下人情,但是抓住机会帮助别人不就把“人情”还上了嘛!我们也应该把心态摆正:每个人都是通过学习和请教,后天地习得技能。
感谢学校给我这次机会,前往世界一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本领域的学术大牛。这不仅提升了我的科研水平,还丰富了我人生的经验、增长了我的见识、开阔了我的眼界、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能够支持更多的博士研究生前往海外受教育、长才干,取得更为丰硕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