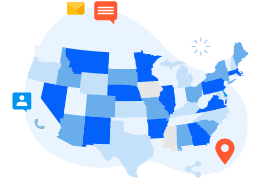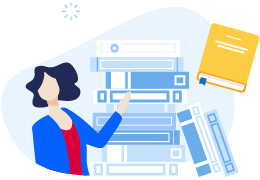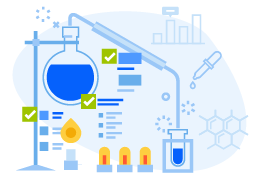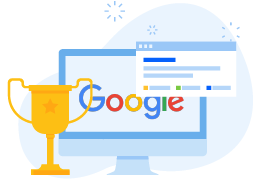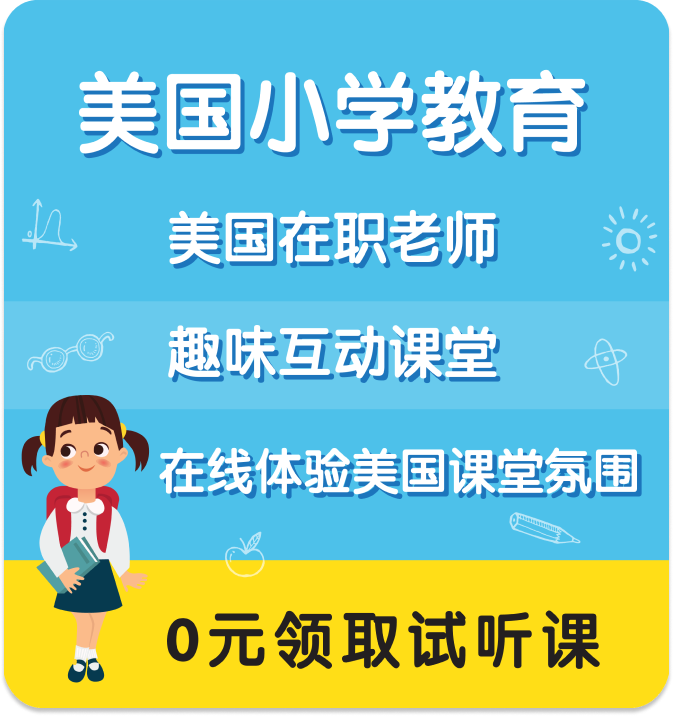树英成长谁在乎一道光熄灭洪嘉琪拉法耶特学院
谁在乎一道光熄灭
大抵写作的人,语言习惯总会有那么一种转折:从一开始桌前摊开的一部矫揉造作的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到堆积辞藻的华丽的抒情叙景,激昂的文字,最后到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平淡。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心态很老的人,正如过去的申请季我在树英度过的“养老”生活:心如止水一般平静,不以offer喜,不以rejection悲。先别人之拿到wait-list而waitlist,后别人之被录而被录。这才是申请季的日常。因为你被录与否,offer与否,都与你的选择有关。当你踏上那条人生的岔路时,你之后的每一步,都是在印证你的选择。有时候,人生就像走在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只有某一天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意识到自己站在如此的高度,或和入口处的告示牌南辕北辙。换而言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走上什么样的路,所以我很自豪的说,我是一个树英人。这是一种认同,是一种归属,更重要的是行为方式上的和谐统一,和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这一趟路上,能有人结伴同行,哪怕是暂时的,也是无比珍贵的。
我一开始并不是很想谈我申请季发生的那些酸甜苦辣,一是因为我的经历太普通了。普通的成绩,普通的活动,普通的文书,普通的waitlist,普通的被拒,和普通的offer,普通的结局,和普通的遗憾。他人的申请季故事远比我的精彩,因为其起承转合,光鲜亮丽,情节跌宕,具有宝莱坞大片的气质,而我的故事,请允许我做出这样的比喻,像一碗被油封住蒸汽的鸡汤,虽浓郁却深藏,却不愿让所有人都能品尝。
但也请您不要紧张,接下来,我就会摆上碗碟和汤勺,在暖黄色的灯光下,与点进这篇文书的你,一起分享一下,那些值得一叙的故事,那些在平凡当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点亮我们意义的光。对了,最后说一句废话:在我反复阅读了多次后,我最终决定删去了大量的议论和论述,今天,我们只讲故事,好不好呀?不好?不行,我已经决定了呢,乖哦。
在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申请季的开始,是Interview workshop和essay class。早早的开始,让我更早的反思我过去的18年。回望过去,我却悲哀得发现,我把最好的,最乐观,最诚挚,真诚而无所保留的自己,留在了记忆里,留在了15岁的那一年。我不知道当我长大了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怀念我的18岁,恐怕不会像我现在这样怀念我的15岁。在我成年的当天,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度过的,我出示了我的身份证,用胜利的微笑,喝下了一杯劣质葡萄酒,晕晕乎乎得,看不大清楚前面的霓虹,心里想着另一片灯火。在申请季开始前,2017年的7月,林肯公园的Chester Bennington用他的方式,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生前的最后一支歌,叫One more light(再多一束光)。9月中旬,我还没有从那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中走出来时,噩耗传来,我一位初中时候的同学,也用他的方式,向我们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压抑的情绪弥漫在心头,山雨欲来之际,我也想不出除了“风满楼”以外更好的词,来描述我的心境。那一刻,一束光灭了。我算不上喜欢摇滚,我也算不上多么喜欢林肯公园,我甚至之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了。What I’ve Done。对于我的那位同学朋友,诚然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系,我和他真的不熟,连点赞之交都没有。然而,在听到消息后,一股巨大的,难以抵抗的无力感和悲痛依然包裹了我。所有人都希望能let it go,连我自己都希望,但是背后的那种挣扎,那种痛不欲生,那种浓郁到令人发狂的情绪,又岂是一句let it go就能排遣消散的。凑巧的是,在他离去的那个下午,我当时正站在学校的天台上,拍下一张张夜景。大片的阴霾,灰蒙蒙的天空,宛如倒下的幕布一样,盖住了整座城市。远方,视线的尽头,一丝丝残阳的余暇,从被楼房遮盖后的地平线渗了进来,宛如一滴血渗入大海后转瞬即逝的一抹粉红。鳞次栉比的楼房,窗帘漏出万家灯火下饭菜的香,点点的,照亮着回家的路。我也曾深夜与他人聊人生,也曾尽自己所能帮助过他人度过艰难的岁月,也曾经给人留下乐观而开朗,阳光而向上的印象。遗憾的是,度人易,度己难。哪怕是到了今天,我自以为自己的心境已经平和如初,但是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做不到,这件事对我来说没有过去。我也不会忘记,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经历过的事情不可能倒装,因为墨迹已干,就像一把狠狠捅进身体的尖刀,留下无法缝补的空腔,每逢牵动伤口都痛不欲生。那些伤口,我悲哀得发现,可能永远也好不了,无论他人多少句安慰,多少陪伴,多少温柔,多少的无微不至。其实也不是没有敞开过,也不是没有寻求过帮助,也不是没有向外界诉求,只是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只是失望的次数太多了,只是失望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出于普遍的正常的自卫机制,我们都将心防越筑越高。其实,正向龙应台女士在《目送》里面表达出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点一样,人都是走向必然的孤独。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推动这个进程,而不是左右这个进程。人是情感动物,人拥有思考的能力和智慧,那么孤独,必然的无可避免的没有退路的孤独,就是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代价。所有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我们没得选。
我不希望会有小朋友被我治愈,所以接下来这段文字,重要性要大得多。有人问我,既然你眼里生活那么糟糕,那么,你怎么走到今天的。我要说,更最要的是过程。既然结局是注定的,既然我们的生活走向定然,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变得更起承转合呢?因为我们活着的意义,或者大多数活着的意义,都不是改变世界。人间路都是向死而生的,没有永恒,只有永别。就像最近我们2018届就要毕业一般,我们会花上所有岁月和心碎,去对抗,去学习,去接受,去迎接这一次一次直到最终的永别,去学会自己告诉自己:“是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在走的时候,体面一点,而我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借用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句,“成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这辈子”。我们这一生,其实,只需要对得起自己,足矣。因为意义,本就是个人的,自己定义的,如果意义当中缺少了自我,就像柜子中缺少了酒。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或许随着人明白得越多,感受得越多,那么ta感知的阈值就会越来越高,而他世俗意义上的感受的能力,感受情绪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我们也会将心里的墙越筑越高。我把这个叫做成长的代价。根据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属性,调整并扮演自己的角色。“一个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好的印象,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保证能够与人,甚至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实现个人目的”。我还记得那个和大姐的谈话,那也是我第一次正面认知,第一次尝试去理解,我的面具,我所扮演的角色,我的为了所谓的“popular”所做出的努力的意义。我们行为,而我们也为我们的行为定义。所以瞻前顾后是没有意义的,患得患失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没有一步是对的,自然也没有一步是错的。我们的人格面具,我们装出来的那个样子,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映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决定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花费一生去达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自己,然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朋友离开我们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疯狂得循环Linkin Park的歌曲,从狂躁,到痛苦,彷徨,到最后的最后,我一遍遍得循环着他的最后一张专辑的主打歌——one more light。坐在回家的车上,外面下着暴雨,滴滴答答得砸在前挡风玻璃上,和不知不觉蕴满了眼眶的泪水一起,晕开了霓虹灯的华彩,却显得更加绚烂,夺目。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从教室里“逃”出去,因为与太多人相处令人感到发疯,内心那翻涌的情绪让当时的我感到彻骨的孤独。爬上学校的天台,立在维港的风里,看着对面的高楼上,海上的游船,看着身边担心的好友。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我们总是不经意间被伤害,我们也总是不经意间伤害了别人。“ 我所有的自负皆来自我的自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于我的软弱。嘴里振振有词是因为心里满是怀疑,深情是因为痛恨自己无情。这世界没有一件事是虚空而生的,站在光里,背后就会有阴影,这深夜里一片静默,是因为你没有听见声音。 ”——《坦白书》。可悲的是,相比于意识到被伤害,我总是花上更多时间,才能明白自己曾伤害过别人。可耻的是,我不敢道歉,大抵是,无论多少的语言,在过去的一切面前都是苍白。我还需要时间,才能长成我心里期望的那个大人,那个具有真正的智慧和博爱的人,也只有在此之后,我才能真正具有完整的,健全的人格,拥有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资格。而在此之前,一切的风雨,一路的艰辛,都没有意义,都不值一提。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告诉自己,“it’s not your fault”,然后我们能顺顺利利的解开心结。但那不是真的,就都是自欺欺人的妄语。难道我们真的无错?无论我们出于什么原因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便是错了。
在这个申请季,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直面了自己。申请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看不到尽头的改文书,一天天逼近的DDL,反复地修改被连自己都感动不了的句子,一大堆要准备的材料和标化送分(垃圾CB经常网络出错)。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人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人,还是自己。我们这一生,就是向死而生,就是在巨大的困难,痛苦,绝望与注定到来的迷茫,恐惧中寻找一道光,寻找一道照亮自己的一道光,寻找那一道可能外人看来不够起眼的,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却是华彩异然的,芳华的,明亮璀璨夺目到无以复加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直直白白,毫无顾忌,一路向前,照到我们每个人心底的一道光。有人跋山涉水,以身涉险,置之死地而复生地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这道光;有人穷尽一生,阅尽书海,在前人浩瀚无垠的智慧当中,苦思冥想,把自己逼入近乎癫狂的偏执,去寻找那道光;更有人,付出了一切,出卖了一切,背叛了一切,好让自己离那道光近一些。其实,那一道光,并不是藏在雄伟的山脉最高的顶峰,藏在连绵的云海雾霭中若隐若现,也不是在浩瀚的大海最深的洋地,埋在堆积的地层化石中等待挖掘,让我们苦苦求索,也不是在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辽阔的人类薪火相传的智慧宝库中,更不能通过交易,出卖任何东西换来。那道光,就像信仰,就藏在每个人心里,等待一个机会,一个照亮我们内心,温暖他人的机会。那一道光就像信仰一样,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福发现自己会有。在这个申请季,以及之前发生的悲剧,事后看来,是一个难得的,逼我直面自己的所有,一切的契机,让我看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光。有些人找到自己的光,也有人,想要变成一道光,一道照进他人心底的光。我曾经试过,我曾经做到过。Cause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feeling low,我一直认为对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开导别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导他人,让自己变成一道光,照亮路。
Cause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Well I do.
不会有学长学姐帮你一起想活动侃大山改Resume,肝Activity list;更不会有Kerri和Will还有Sarah陪你辛苦的Brainstorm,在巨大的workload间隙陪你聊人生,感悟和自己的理想;没有大姐和你一起聊学校,school research;没有老板时不时凑头凑脑过来盯着你电脑界面不让你玩手机;没有璐璐和你一起填写personal profile,催文章,DDL,和你一起吐槽某些学校的不靠谱;没有佳易姐催你好好考试,标化;没有颖杰姐帮你往邮箱里放活动资料;也没有元元姐和她的NeiNei一样带来莫名其妙的欢乐(划掉)。
正如Ciao常说的那样,来是增肥的。早上抱着电脑来到小客厅里面,往沙发上一瘫,没过多久就有人拿着手机过来:“奶茶要么?炸鸡吃吗?中饭要不要一起订?等会去楼下超市一起么?…”还有许许多多有一茬没一茬的闲聊,排队抢office hour,互相嫌弃白眼然后告诉你这段文书ta自己的思路衔接…可能这都是申请过程当中一些很琐碎,很细小的事情,可正是这些事情,组成了树英的生活气息。如果说申请季就像大家划着小船,点着昏暗的摇摇晃晃的油灯,划过仿佛永无尽日的黑暗,朝着远处摇摇晃晃的灯塔前进,那么在树英,我们就是一支船队,互相点亮大家周围的水域,鼓励周边的伙伴抖擞精神,重新上路。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不是朋友,但只需要这些人在那里,那就是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对我而言非常难得,难寻的感觉,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是在这个寻找答案,迷茫而慌乱的时间里,想要的答案的一种诠释方式。
当然,我还是想在这个时刻,在申请季结束的时候,回顾这一步一步走来的道路,和树英的故事:
高一时候寒假托福班被虐到死去活来,两年过去我居然当上了助教;
高二暑假的SAT班上忧心忡忡,但是成绩终究还是考出来了;
暑假被老板拉到小房间里面的那场争执,和Kerri紧随而后的安慰;
极度累人烧脑的Essay Class里面无数的插科打诨的欢乐;
与好友在College Fair现场伪装乔治城大学招生官;
Game night的晚上被迫一起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告诉我:“我觉得你的这篇写得很好啊”的Hanwen学姐,“你标化一定能考出来的”Stella学姐;早在暑假就帮我们做好Activity list,resume思维的学长学姐助教,Stella,朱禹同,Hanwen,Joseph,Serena,Sabrina,让我整个申请季没有后顾之忧;
感谢暑假Essay D 班的小伙伴给我们就,感谢大姐和Sarah对于我的personal statement的至关重要的帮助;
感谢申请的几个月间一起在树英骂过人,吐过槽,吃过饭,请过客,打过牌,一起养生养老修行的小伙伴们:Gisele,Ciao,Hank,Chloe,老吴,Roger,Emma。
感谢在自己申请结束后还给我们加油打劲的小伙伴们,欢乐总是苦恼的调节剂;
感谢DTR把我们聚到了一起,让这段艰苦的时间,精彩得令人难以置信。
最后,还要感谢父母近乎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在申请季几乎完全放手(给钱以外hhh)的态度让我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于文理学院的爱。这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结语:
大抵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人,本就没有棱角。
我已不再年轻,亦不再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