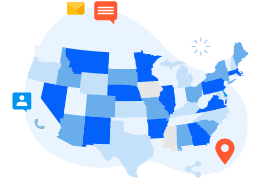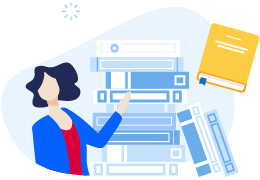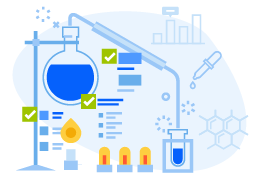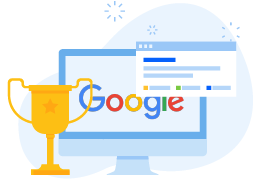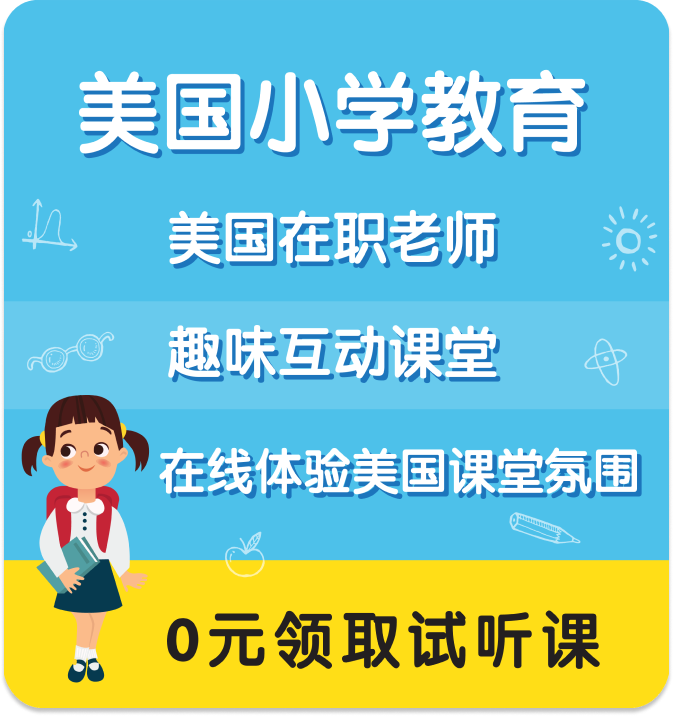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专访斯坦福大学教授亓磊未来需要可逆的基因编辑技术
11月28日中午,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表报告并回答提问,介绍了大致的研究情况,并回复了一些关于该基因编辑的医学必要性、监管情况、经费来源、知情同意书和未来措施等问题,但由于大会时间有限,公众关注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详细答案。
两天前,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是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据悉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为“CRISPR/Cas9”技术。
贺建奎讲述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该事件在全球学界引起巨大轰动,不少科学家纷纷表示质疑与反对。与此同时,在媒体与大众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热度高居不下,并引发了不少恐慌。
对此,小WE姐特别邀请了2016腾讯WE大会嘉宾——基因编辑领域专家、斯坦福大学的亓磊教授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解答。
独家专访
亓磊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生物工程系教授
亓(Qi)磊长期致力于基因技术和基因治疗研究,发明了基因调控技术包括CRISPRi基因抑制、CRISPRa基因增强,以及CRISPR-GO基因重组技术。拥有专利20多项,是CRISPR在中国和欧洲专利的共同发明人。他在国际刊物《细胞》《自然》及子刊发表多篇论文,论文引用近万次。曾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独立科学家奖、皮尤学者奖、斯隆奖等。(实验室网站:http://med.stanford.edu/qilab)
WE:这次基因编辑婴儿究竟有没有科学或者技术上的突破?
亓磊:从目前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个研究没有任何科学或技术的突破。其实基因编辑并不是一项新的技术,在科学界已经应用了近20年。之所以一直没有用于编辑人类胚胎来治疗疾病,是因为这项技术还远未达到安全可用的程度。该技术仍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目前国际主流的基因编辑研究方向包括:如何将基因编辑的精准性达到医学的标准,以及如何通过不改变基因来治疗疾病(即非转基因技术)。虽然目前研究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但是距离医学应用特别是编辑人类胚胎还有很大的距离。
该事件中,科学家采用2013年发明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直接将人胚胎的一个关键基因删除,其实技术上没有任何突破,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开展该类实验。他们只是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情而已。同时,该团队没有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精准性和基因删除的长期副作用进行评估,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不顾医学伦理的行为违反了全世界科学家都应遵循的科学道德准则。
WE:这次事件引发巨大争议和批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亓磊:目前基因编辑主要基于2013年出现的第三代技术,称为CRISPR技术。虽然近些年CRISPR技术被称为“基因魔剪”,但是其“魔力”是有限的。确切地说,CRISPR技术只是对于前两代技术的一个改进(注:前两代技术为ZFN锌指核酸酶和TALEN转录激活样效应因子核酸酶技术),降低了基因编辑的门槛、成本和周期,但是其应用于胚胎编辑仍然是不够精准的。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除却被编辑的基因外,该技术存在脱靶问题,可能对其余基因产生永久的更改,而绝大部分更改都是破坏性的。另外实验证明经过CRISPR编辑过的细胞会引发细胞凋亡。基因编辑的安全性还需要系统的考证。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争议和批评,在技术层面来说,有如下原因:
1)CRISPR技术具有脱靶效应:即除却想要修改的基因外,还有可能对编辑对象的其余基因造成修改。这种修改不可控,是随机的,而且一旦发生无法修复。在没有评估风险的情况下,直接将该技术用在人的胚胎并产生婴儿,是将婴儿未来漫漫人生路置于多种未知疾病的风险中,非常不人道。
2)基因编辑的速度是缓慢的,慢于受精卵早期的发育速度,从而会造成嵌合体(即有的细胞被编辑、有的细胞没有被编辑),因此不可能达到预防艾滋病的期望。这在之前的小鼠实验就已经被证实:如果将小鼠受精卵内的黑色素基因删除,生出的小鼠是一只黑白相间的杂色小鼠。这是因为有的细胞黑色素基因被删除,有的细胞该基因没有被删除。同样的道理,生出的小女孩的不同细胞内有不同的修改,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对艾滋病的预防。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上被称为“马赛克”现象。目前基因技术无法消除马赛克现象,因为技术尚未实现100%的细胞编辑。
3)已有实验证实基因编辑过的细胞会造成抑癌基因的缺失,进而增加致癌的可能性。这无疑又增加了这对双胞胎未来的疾病风险。
4)永久不可逆地删除基因来预防和治疗疾病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人类的基因一般有多个功能,比如在该研究中删除的CCR5基因虽然是HIV入侵人体的一种通道,但是却赋予了人类对于其他病毒的免疫力。该基因对于人体的发育过程也可能有重要的功能。为了预防一个功能出错而将该基因彻底删除就如同因噎废食,是大错特错。
因此,基因治疗技术或逐渐兴起的所谓“基因手术”,其突破方向不应是单纯删除一个基因,而是需要整体、科学地保证基因编辑技术的精准性、安全性和可控性。在尚未达到安全的基因编辑情况下强行进行人胚胎实验,并活生生的将基因编辑人带到了人间,是一种违背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
WE:这个新闻如果属实,这对双胞胎的成长有什么隐患?是否真的会对人类基因库造成影响?
亓磊: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目前所知的基因编辑是不可逆的。当该技术用在人胚胎上时风险非常大:一旦发生错误,轻则会诱发被编辑人的自身疾病或早亡,重则会造成所有后代的新型遗传病。可以说,目前的基因编辑应用于生殖细胞或胚胎时,任何编辑错误都是永久的、可遗传的,其潜在危害远甚于毒品和药物滥用。
其次,人类有2万多个基因,很多基因都有其存在意义。譬如在南方地区有人携带造成贫血的基因突变,但同时这种基因突变大大降低了疟疾感染的致死性。人类基因就像一个积木塔一样维系着平衡。如果把一块积木强行去掉,很有可能会造成癌症、免疫疾病、加速衰老和遗传疾病。基因编辑影响的不只是被编辑本人,而是所有后代,甚至是整个种族。因此,当这对基因编辑婴儿出现的时候,我们担心其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对于这对双胞胎的未来成长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疾病风险,其心理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毕竟是人类,是有思维、可接受心理暗示的同类,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疾病,很难评估。希望未来能在关注这对双胞胎姐妹的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对其加强心理健康引导。
WE: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应用前景如何?用于临床治疗的案例多吗?
亓磊:CRISPR-Cas技术诞生至今已有近6年,但该技术尚存在一些弊端。未来仍有几大门槛要跨越:如何提高编辑的精准性、如何实现可逆的基因编辑,以及如何不去改变人的基因序列而实现疾病治疗。未来的基因技术必须是可逆的,可以容错的,才有可能用于医学治疗。目前基于CRISPR的临床治疗全部处于实验阶段,而且都是改变人的体细胞。脱靶和免疫排斥是目前需攻克的难题。
大家目前已经熟知的是基因编辑技术,即永久改变基因序列的技术。其实还有一种和此技术并存的技术称为基因调控技术(即CRISPRi技术) 。基因调控技术是一种可逆的基因编辑技术。基因调控技术在不改变基因的前提下,通过增强或抑制基因量来实现对基因功能的调控,实现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技术具有可逆性,可以将表达改变的基因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还原。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基因调控技术可以在人体受到HIV感染前将CCR5基因关闭,并在危险消除后再次打开。以此类推,基因调控技术很有可能更安全地用于其他基因和疾病。
WE:据说中国之前就已经有86人接受过基因编辑的临床治疗,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什么情况?
亓磊:关于目前网上所说的中国之前就已经有86人接受过基因编辑的临床治疗,这是在成人的体细胞里进行的编辑。体细胞不同于受精卵,其基因突变是不会遗传给后代的。所以最糟糕的情况是被测试人本身受到影响,但不会影响后代。这完全不同于在该事件中对受精卵的基因编辑。在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一些临床实验在高度监管下正在进行,譬如一些遗传病(如地中海贫血)或癌症免疫治疗(如CAR-T)实验。
WE:基因治疗的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审核严格度是否一样?标准是什么?中国是否更为宽松?
亓磊:2015年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编辑的事件,引发全世界科学家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广泛讨论。在华盛顿基因编辑峰会上,以中国、美国、英国为发起国,达成共识:鉴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还存在各种技术层面、社会层面以及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其安全性目前还无法估计,且一旦被编辑的基因进入人类基因库,该影响是不可逆的,不受地域限制的,因此,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是应该禁止的。对于体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在实验室范围内是谨慎鼓励的,确保其影响范围是可控制的。
中国科技部2003年就有严格的规定,即关于人胚胎研究的“14天规则”: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显然,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该研究团队严重违反了中国科技部的规定,也打破了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承诺,反而有可能导致该技术的临床应用研究的倒退。
WE: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基因研究和基因治疗领域领先于美国,你怎么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亓磊:不可否认,中国在基因研究和基因治疗领域的确做了大量的基础和应用工作,但中国和美国在基因研究和治疗领域的侧重略有不同。从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美国的基因研究更偏重于技术的创新和坚实的基础研究,中国的基因研究更偏重于应用,包括如何将已有的技术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中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但是不论是怎样的研究,科学是国际的,科学家身负重大的责任和期望,不应该亵渎自己的职责而使用科学技术做出对人类有害的事情。
事件回顾
基因编辑婴儿首先由外媒报道,引起一阵哗然。而后人民日报跟进报道。至此,此事件开始全网发酵。
据披露,贺建奎所做的这项临床试验已经通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但有业内人士指出,此医院是莆田系医院。相关人员也随后进行澄清,称对此事“没有印象”,签名或为伪造。
随后,中国卫健委、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卫计委、深圳和美妇科医院纷纷对此发表声明,表示“不知情”、“不属实”、“将会彻查此事”等。南方科技大学也发出声明“贺建奎已停薪留职,研究工作学校不知情”——但在曝光的知情同意书中显示,该项目经费来自南科大。(注:最新消息是,贺建奎在峰会上表示,一部分经费来自于学校的start funding,但学校对这项实验并不知情。)
与此同时,122名中国科学家联合发声,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表示“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我们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46名律师也联名发布律师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和不安的同时,建议司法机关介入,依法追究相关联方责任”。
截止目前,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1篇文章)及Nature(3篇文章)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并登上官网首页。
随后,贺建奎本人对公众质疑进行了回应,并录制了一个英文视频。其中,他表示“We believe ethics are on our side of history”(坚信伦理将站在我们这边)
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所运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为“CRISPR/Cas9”技术。而这项技术的先驱——Jennifer Doudna、张锋和David Liu,对此事也表明了态度。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Jennifer Doudna表示:“假定今天的新闻得到证实,这使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限制更为紧迫,我们应该将人类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限制在仅用于确切的未被满足的医学需求上,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医学手段,这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倡的。”
麻省理工学院理学院终身教授张锋,曾带领团队率先开发了用于天然微生物CRISPR-Cas9系统的真核细胞的基因组编辑工具,对此表示:“鉴于目前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早期状态,我赞成暂停植入编辑胚胎的临床试验,直到我们提出一套深思熟虑的安全要求方案。”
David Liu是哈佛大学/Broad研究所的化学生物学家,曾研发出一种Cas9酶的变体,是基础版酿脓链球菌Cas9酶(SpCas9)的“升级版”。他表示:“最近报道使用CRISPR核酸酶编辑人类胚胎中的CCR5,这严重违反了道德规范。最重要的是,编辑过的人类婴儿是在没有独立的科学和伦理专家,相关监管机构和理事机构的充分参与的情况下产生的。”
尽管现在国内主流舆论近乎一边倒地谴责,但在公众的匿名投票里,却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结果。在微信“搜一搜”热门话题榜中,有过半的人赞成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以期免疫某类疾病。
此外,据 Nature 报道,调查显示,许多人对能治疗致病突变的胚胎基因组编辑持支持态度。7月,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发布了一份由319人参与的调查。将近70%的人表示支持基因编辑,前提是这项技术能让无法生育的夫妻生下孩子,或能让夫妻改变胚胎中的致病突变。上个月,一项由4196名中国公民参与的大型调查显示,如果目标为预防特定疾病,受访者对基因修饰的支持度与前述英国调查类似。但受访者反对将基因编辑用于增强智力、运动能力或改变肤色。
◆ ◆ ◆
2016年,亓磊教授曾在腾讯WE大会上为我们分享过基因编辑和调控技术的前沿研究。他最后有句话让所有观众心中一热,小编在此也特别想再次分享给大家——
他说:“做生命研究的初心是‘医治伤患’、‘逆转时间’、‘改变命运’。”
关于基因编辑婴儿,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分享~
来源:腾讯WE大会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Dreamgo网站,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copyright@dreamgo.com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info@dreamgo.com